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認知中,與微軟公司關聯的最知名的中國人是張亞勤,曾經的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后來去了百度,轟動一時。
大部分人不知道,微軟公司最高級別的華人高管另有其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
每周五下午,沈向洋和其他10位微軟高管會出現在會議室,開一個長達4小時的會議,討論解決全球公司一周以來的所有關鍵問題,然后上報CEO。在微軟內部,他們被稱作“十一常委”,把握著這家巨頭的步伐和走向。“十一常委”各有分工,沈向洋負責的是這家世界最知名軟件公司的研發。
到今年,沈向洋已在微軟工作20年。自博士畢業,他便一直在微軟工作,成為其核心管理層唯一的大陸華人,也是美國科技行業職位最高的華人。
在學術圈,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Harry Shum。作為計算機視覺和圖形學研究的世界級專家,Harry從全美計算機專業排名第一的卡耐基·梅隆大學畢業,師從圖靈獎獲得者、著名計算機科學家Raj Reddy。他的同門師兄還有李開復和洪小文,后者是微軟亞洲研究院的現任院長。
沈向洋與張亞勤同年出生,一個13歲進大學,一個12歲上中科大。不過,他對《財經天下》周刊記者否認自己是天才,“你我都是普通人”,甚至笑稱幸虧有研究稱孩子智商主要遺傳于媽媽,所以他不用背負壓力。但他說,自己見過許多聰明到“刻骨銘心”的天才。
實際上,在和李開復、張亞勤一同創建微軟亞洲研究院的歲月里,他親手帶著一批剛畢業的高校學生,將科研這件事做得如魚得水。2002年,他和所領導的圖形圖像組一戰成名,在全球計算機科研領域最富盛名的國際圖形學年會SIGGRAPH上發表了4篇論文,讓微軟亞洲研究院在學術界站穩腳跟。2004年,微軟亞洲研究院被評為“全球最火實驗室”。
這是他們在辦公室不舍晝夜、夜不歸家拼來的結果。有一天,沈向洋和同事們正自嘲“忙成了狗”,前任微軟亞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堅路過聽見,看了一眼這群胡子拉碴的理工男,說:“我看根本是豬狗不如。”眾人爆笑。
后來,王堅離開微軟亞洲研究院加盟阿里巴巴。李開復、張亞勤等人在離開微軟之后,也成為各自領域的領袖。作為留守者,沈向洋于2007年重回美國,并在2014年升任執行副總裁至今。
沈向洋習慣讓員工直呼其英文名Harry,與他接觸過的人都認為他“極nice”。給實習生講話時,他會用自己大學時期籃球場上“單手喬丹”的外號自黑來做開場。遇到員工恭維,他會即刻打斷,提起他最近教了美國大使一個詞“Mapi-ology”(馬屁文化)。一個政黨領袖曾教了他這個詞,說弄了半天什么也沒做成,只培養了一批人會Mapi-ology。說完這個故事,他與被調侃的員工一起大笑,恭維終止,議題繼續。
隨和是沈向洋待人的方式,而他實際的工作作風,則是另兩個字:強悍。他會在凌晨5點就進入工作狀態,回復記者的工作微信;也會在主持面試的最后一輪,兩位面試者不分伯仲之際,干脆看看誰的飯量更大——因為“這行很苦,不強悍做不了”。
今年,沈向洋年滿50歲。他最近的愿望之一,是成立微軟亞洲研究院院友會,將曾經一起“豬狗不如”地干活打拼的那幫人聚起來,再提供一個大家交流的平臺。
比起散落全球的院友,還有一群同樣絕頂聰明的大腦離沈向洋更近:他執掌的全球7所微軟研究院。在過去15年間,全球權威性計算機國際大會上,微軟研究院的得獎論文數量是全球第一,遙遙領先,其后才是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大學。
1991年,第一所微軟研究院,位于美國微軟總部的雷蒙德研究院成立。其后20多年間,軟件巨頭用難以計數的支出建起了龐大的聰明人“庫存”,網羅住超過1000名計算機領域的頂級科學家,包括大量圖靈獎、麥克阿瑟獎、菲爾茲獎得主。
“科研領域有很多天才,我很幸運見到了一些很聰明的人,刻骨銘心的聰明。”沈向洋說,他正在竭力盡量快、盡量廣地“淺度學習”——微軟研究院有很多方向,身居高位的沈向洋要對整個計算機科研發展有很好的大局觀。為此,他需要不斷大量地閱讀交流學習,如海綿吸水,再抽絲剝繭。
這是一個在科技創新最前沿工作、被天才環繞的人,強悍、親和、邏輯縝密、語速飛快,日程表排得爆滿但仍然神采十足,你時常能感受到他內心青春似的激情。他說,對于公司來講,年輕不光是年齡問題,還是心態問題。對于他本人來說,也正是如此。
以下是沈向洋的口述。
聰明人很多,但如果只是聰明也沒有什么了不起
為什么我會留在微軟?告訴你我當年的那種激動。1996年,我加入美國微軟研究院,那時我做圖形學,圖形學領域最牛的一個人叫Martin Newell,他做的一個茶壺的渲染,經典到任何圖形學的演講里一定有那個茶壺。
加入微軟研究院以后,我發現他離我只隔著4個辦公室,特別激動,當時就沖到外面給老婆打電話:“Martin Newell離我只有4個辦公室!”因為我實在是非常敬仰他。他每天都穿同樣的綠色毛衣,就像扎克伯格、喬布斯等人的作風——也許成功人士都是這樣。
Martin Newell是超級天才,而我不是天才,你我都是普通人。微軟研究院當然有天才,而且每一代都有聰明的人出來,所以不是一兩個,而是有相當數量的聰明人。這些人表現得都很低調,而且各有各的聰明方式:一種是明面上的,就是什么題目都能快速解答;另一種聰明,是他能看出來什么東西能做成,并且沉得住氣一年一年地去做。
比如王堅,非常獨特的一個人,他原來是學工業心理學的,但是他非常熱愛計算機。他想問題比較怪,能夠想到其他人不會去想的思路,我跟他在一起學習到了很多東西。
年輕一代則更多,比如周昆,最年輕的長江學者,最年輕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現在是浙大的教授。他只有30多歲,屬于中國年輕一代科學家里面的殺手級人物,也是唯一一個在SIGGRAPH上發文比我多的人。他很強,非常強悍,非常聰明,因為做研究很苦,不夠強悍扛不過去。我非常喜歡周昆。
我還有一個非常聰明的學生叫劉徹,現在在谷歌。他來面試的時候,簡歷上寫著:全國數學競賽一等獎,全國物理競賽一等獎,化學競賽一等獎,全國千名小畫家之一??我就問他:你一輩子有沒有得過二等獎?他想了想,說還真的沒有得過二等獎。我說,那這樣子就像是我的學生了。跟他在一起,我向他學習。
聰明人很多,但如果只是聰明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我反而更喜歡一種能夠后天培養出來的。我最喜歡的一個學生叫王嘉平,他的本科是很普通的一所大學,寧波大學。有人向我引薦了他,他是真的聰明,最厲害的就是博士畢業論文被SIGGRAPH選中,當年還得到全國百佳博士論文獎,是那一年唯一一篇計算機類的。獲獎以后,中科院計算機所請王嘉平給師弟師妹們做一些分享,他于是講為什么在微軟亞洲研究院可以做這么好的科研,怎么能寫這么好的論文。
所以你看,一個好平臺何等重要。不久前我回國跟大家說,我們亞洲研究院有兩件事是非常值得驕傲的:第一是環境,我們這里的待遇很好,但更重要的是這個環境里有很多比自己更聰明的人;第二是自由,就是大家可以選擇自己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
作為一家公司的科研負責人,我能夠提供的也就是這兩點。我當然希望中國其他的機構也能做到這樣,甚至比我們做得更好。
最近,很多人來微軟亞洲研究院挖人,王嘉平也在不久前離開了微軟,我覺得也很正常。如果外面有很好的機會,每個人就會去走一條不一樣的道路。我們辦研究院一定要明白:這個機構為什么要存在,為什么可以存在,一定要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在里面。
當然,我們并不是一直都有很好的狀況。2014年,我們關閉了硅谷微軟研究院,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定,背后當然有種種不便于對外解釋的原因。這件事情對我個人的沖擊也很大,因為一直以來我很自豪,覺得自己做了這么多年科研,也算是做得還行。結果,在我任上,卻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看上去跟科研背道而馳的決定。
當時的硅谷研究院里,很多是理論計算機科研的專家,這些科學家的圈子非常團結。事情發生后,他們聯合起來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我,質問怎能做出這樣的決定。聯名的人都是知名學者,很多也是我的朋友,他們的話我們當然要認真聽。所以我向很多資深的教授請教,10天后,我回了一封信。
寫那封信的時候,我壓力很大。第一,我剛上任執掌微軟的科研還不到一年時間,一家研究院就被關掉了;第二,我很尊重的老教授給我寫信說這完全是一個錯誤。
最終,我在回信中情真意切地剖白:首先,解釋整個公司的研發被砍掉了百分之多少,所以我們的部門同樣也沒有幸免、也不該幸免。其次,我承認關閉的決策是我做的,并且我當然也可以做其他的決策,但是最終做了這個痛苦的選擇,決定關掉硅谷研究院——迫于種種原因,只是我不能解釋。
但是,我堅決強調的是:關掉這一家研究院,并不代表微軟對“做研究”這件事情有任何的懷疑或動搖。在那封信的結尾,我引用了微軟研究院創始人Rick Rashid博士的話,再次保證我們整體對“做研究”的這項承諾是永久的。信發出之后,事情基本上就平息了。
到今天,事情過去兩年了,至少我自己覺得,微軟研究院在各方面都比兩年前更強了,不論是科研成果或是公司的影響力,我們對整個工業界的影響比以前更大了。Rick Rashid博士前幾天剛剛宣布退休,我想自己對得住他的承諾。
我不同意微軟創新能力弱于谷歌
谷歌在互聯網領域是家偉大的公司,但就此評價微軟創新能力弱于谷歌,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原因是我以及大多數人都不了解谷歌,很多時候大家能夠觀察到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以此形成對一家公司的印象。而我足夠了解微軟,我們總是很低調。谷歌的搜索當然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微軟也有很多好東西,沒必要放一起比。
小米手機本身好嗎?它很成功,賣得很多,那就很好。還有人覺得論起成功,小米和華為都不算什么,最了不起是vivo和 OPPO。
其實,最了不起的就是各自走一條不一樣的道路。這也是為什么做研究很了不起:你不用擔心別人如何,只要想想自己要做什么就可以了,只要不是抄別人的,你就一定能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一定要跟谷歌對比的話,從2007年開始負責Bing確實是我最痛苦的一段經歷。當年,微軟下定決心做Bing,砸了很多錢,公司的精銳部隊都進去了。在微軟的人才庫中,我和薩提亞(Satya Nadella,微軟現任CEO)都是戰略預備隊,被投到戰場前方。我倆以前都不是做搜索的,2007年,薩提亞被任命負責Bing團隊,我也被調離微軟亞洲研究院,回到美國總部,成為Bing的首席科學家。
一旦從研究轉向業務,就拉開了一場商業馬拉松:做學問只是其中一部分,然后要做產品、市場、銷售,最后還要賺夠錢來做下一個(項目)。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不像做科研一年就投稿一次,咬咬牙把論文弄完,你就可以放個假喘口氣再繼續。一旦開始商業馬拉松,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今年賣了5000萬臺,明年賣了8000萬臺,后年只賣7000萬臺,大家就會覺得這個公司有問題,怎么只賣了7000萬臺?
這樣的長跑途中,肯定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所以我們要夠強悍。我喜歡的一些學生也是這樣的,很多人比他們還聰明,為什么沒有成就呢?因為不夠狠。(要有成就)你就得咬牙,強悍地挺住繼續。在Bing的7年時光,我也都靠此挺住,一路追著谷歌這樣的對手跑起馬拉松。
大概2013年,我快要從Bing團隊退出的時候,我見到了拉里·佩奇(谷歌創始人)。我當然對他很敬仰,主動找他握手,再做自我介紹。然后他就笑笑說,Harry,你們做得還算不錯(not too bad)——“not too bad”,這三個字是我在Bing打拼7年以來得到的最大表揚,比蓋茨、鮑爾默給的肯定還重要。當然,這可能是句客套話,但頓時又讓我激起一股勇氣,讓我知道這場搜索之仗終歸還要繼續。
如果往負面去想,在谷歌已經全面壓制住搜索市場的時候,你還要硬著頭皮去從頭開始與之競爭,背負所有的壓力干7年,這一定是個痛苦又漫長的過程。但是往正面想,一輩子有多少這樣的機會可以去學習?有幾個人有這樣的機會能帶著幾千名兄弟跟谷歌打一仗?
我們至少沒有落荒而逃。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這樣:你要去打一仗,這一仗也不是你說要打的,但又是必須要打的,所以總得有人去,那就只有奮勇向前。
當初決定投入那么多的資源去打搜索的仗,聽起來是很重大的決定,其實沒有那么復雜,很多人想太多,但想太多就完蛋了。實際上,這么多年,微軟在整體的產品布局里,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情就是下定決心做Bing。
不光因為它現在已經站住腳了,Bing從去年開始就掙錢了,預計接下來每年還會保持30%的增速,我們已經有了超過40億美元的收入。這些數字都只是成功的一部分而已。在Bing這件事上,真正最了不起的是,你一定要看世界的趨勢。這幾年發生的事情非常簡單,首先就是出現了互聯網,然后出現了移動互聯網,接著就是云的誕生。公司一定要能看清這些事情的本質:互聯網的出現改變了知識積累的過程,知識積累中最關鍵的就是搜索引擎。
一個搜索引擎對微軟戰略上的重要性,在于連接起以后所有人工智能的東西,就好像每一個Office的新版本都聯系在一起。一切生產力相關的東西,不用搜索引擎連起來是不行的。比如你要知道有關世界的知識,可能會去看維基百科,如果沒有搜索引擎,這件事情就非常難。更別說每天有海量新東西出來,很多事情是動態的,更需要相互連接。我們很幸運,Bing能夠做得“還不錯”,并堅持至今。
很多東西在一開始是看不透的,比如微軟做手機,還有Windows對平板免費這件事,要早兩年的話就會更成功。這些都是馬后炮,在當時,面對那么多現有的業務,你很難看透。
微軟執行副總裁沈向洋
一個人能干好一行就很了不起了
我很相信一句話,叫“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人們常說我的興趣是這個,但我在浪費時間做其他事情。在我看來,這些都是托詞。誰都不知道這輩子到底適合做什么,那么多職業也不可能都做一遍。
最重要的是,不管你做哪一行,一定要(給自己)有正反饋,就是小表揚、小鼓勵,不然很難繼續下去。我的很多學生后來就不參加SIGGRAPH了,因為論文總是不中。最后殺出來的學員,都是夸出來的。我有個非常優秀的學生叫孫健,他每年投兩篇中兩篇,最后一年投兩篇中一篇就沒興趣了,從此就不參加了。
我現在已經很少做一線的事,但還是堅持看一些自己喜歡的課題。站在我這個位置,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要學得快、學得廣,因為微軟研究院有很多方向,我必須對整個計算機科研發展有很好的大局觀。
舉個例子,兩年半之前,我不知道量子計算是什么。現在,我個人的判斷是10到15年以后,量子計算一定會應用開來。所以上星期,我們宣布成立微軟量子計算部門,還調了一個公司副總裁專門負責這件事情。我們下定決心要進入這一行,這也是我過去這段時間學習思考得出的結論。
從整個業界來講,現在開始也要對量子計算這件事情充分重視。不是說量子計算機馬上就能出來,也不是說它馬上就能解決很多問題,但大趨勢已經非常明確了,這是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怎樣去學習,從而做出決策?你必須要學得很廣、理解得很快。個中訣竅沒有別的,就是硬干!你必須多讀東西,所以一個很重要的能力就是快速閱讀能力。在這方面,我最佩服的就是蓋茨。他有句話,叫ferocious reader,讀得很兇猛。
一年半前,跟蓋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我問他一年讀多少本書?他說70本,平時平均一個星期讀一本,暑假和過年的時候還有reading week用來讀書,那段時間他就會讀十來本,所以一年能讀70本書。
他能讀70本,我們至少要能讀個7本、10本吧。實際上,我一年大概能讀10來本書,至于論文就看得非常多了。我現在管研究院,負責公司技術方面的工作,所以有很多機會可以快速學習。有很多組在他們的領域已經做得很深了,但是要深入淺出地向我講明白,于是我就很幸運地能學到很多東西。每周,我專門有兩小時做Technology Review,去了解不同的課題。最近我決定主抓人工智能,于是接下來每周都會用兩個小時去專門審視人工智能的所有方面。
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快速閱讀理解能力的培養。哪怕那件事你本身沒有興趣,也要去做,就是我講的一定要“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
人們喜歡談“深度學習”,那是對機器的,放在人身上都是瞎忽悠,沒幾個人真能做到。我們更應該做的是淺度學習,你不可能對什么東西都有深度理解,一個人能干好一行就很了不起了。
快速淺度學習的能力,才是一個人真正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不僅對于高管,對于其他所有人也都需要。就好像一個學生不可能所有學科都很好,他有兩門課很好,就很了不起了,如果第三門也很好,那就非常了不起了。但是這樣最多也就能保持到高中,再到大學就不可能了。上帝很公平,你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不能同時專注太多東西,但至少可以對很多東西保持一定了解。
最終到底選擇哪些事,有可能只是看當時的風怎么吹,我們其實大都是風口上的豬。比如當初我在專業上選擇計算機,完全是偶然的。高考填志愿時,我父親回到家,拿了份《參考消息》,說你應該報計算機,報紙上說有個東西叫計算機。那是1980年,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計算機為何物的時候。結果我本科還沒學到計算機專業,后來去了卡內基梅隆計算機學院,又進了微軟,才算是入了行。
能夠創造潮流、引領潮流的人是極少的,絕大多數人應該學習的是發現潮流、趕上潮流的能力,這是很重要的。你去問那些真正引領了潮流的人,為什么能夠引領,他也講不出來,往往是人去配合環境。
永遠不能失去危機感
從小到大,其實我一直是想當大學教授的。現在在企業里,也許年紀大了,退休后應該去做個小學校長。因為那時候做科研已經做不動了,在公司待著,決策推出來是錯的,程序編出來有很多BUG。那你總得想想,一輩子這么多的經驗,怎么樣能傳授給下一代?我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可以做貢獻的地方。
可能因為在教師家庭長大,我對教師這個職業是充滿著敬仰的。人類的進化發展,其實都是一代代人傳承而來的。傳承也是我們對下一代的義務。有些人像我一樣,能在一個位置上影響到一大批學生,我覺得很幸運,很自豪的就是一輩子帶了很多很優秀的學生。
怎樣帶出優秀學生?具體到公司里,就是所謂人才觀。曾經,我確實有些想法,比如所謂“三好學生”——數學好、編程好、態度好,或者有前兩好也就夠了,態度可以培養。到后來,我覺得每個學生還是不一樣。做一流科研,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沒有悟性,有些人突然就悟了,有些人弄了半天也不悟,突然一悟又非常強。
后來我跟人開玩笑,說收學生就像生孩子,收了就得培養出來,不能塞回去。有一次我跟太太討論怎樣培養孩子,很頭大,想來想去也沒什么高招。我們是相對富裕的家庭,孩子連吃苦的機會都沒有,不像我們小時候在鄉下長大,是完全不一樣的成長環境。
最終我們覺得,可能只有兩件事情是比較重要的:第一就是正直、誠實,首要還是教會小孩正確的價值觀。第二就是勤奮,要孩子明白任何東西都要靠自己努力刻苦爭取到。
對待人才也一樣。你考察一個人,他能在微軟通過三輪面試,IQ肯定都沒有太大問題,你就要看看這個人有沒有一種自己想努力向上的精神。我喜歡學生和員工保持一種饑餓感,這個很重要,這樣他才能不斷地保持向前的動力。
有一年,我在SIGGRAPH上出了非常多的文章,一個在美國做教授的朋友打電話給我,開玩笑說我中了這么多篇,別人會恨我的。放下電話,我想,為什么我們還這么努力呢?可能因為我們是中國最后一代吃不飽飯的,永遠有一種危機感和饑餓感,而一個人永遠不能失去危機感。
那時候我想,也許微軟真的是這樣一個環境:不很努力拼命做科研的話,過兩天也許就沒有你了。結果還真的這樣,接完電話過了幾天,我就被趕出研究院去做產品(進入Bing團隊)了。
回到美國做產品后,我發現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簡單的,就是people bring people。人與人之間的吸引力,才是聚攏人才的不二法門,一個行業大牛在這里,你能跟他學幾招就很了不起。特別是對于年輕人,還在快速成長期,非常希望能跟身邊的人學習、吸收很多東西,大家找工作時都希望能有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打造這樣一個環境,讓大家覺得來這里能夠學習更多東西,事業更上一層樓,甚至有人跟你一起合作,提供充足的資源,讓你做更大的事情。
如果我們不創新就會被顛覆
任何一個單位永遠都需要補充新鮮血液,這也是我很喜歡大學的原因。大學里的平均年齡是一個常數,一屆人年紀長大了,又換了一屆,新人進來又是這個平均年齡,非常了不起。
對于公司來講,年輕不光是年齡問題,還是心態問題。我非常喜歡我們CEO講的Growth Mindset(成長心態),他說不要老覺得自己什么都知道,而是說什么東西我都可以再學習,前者叫做knower,后者叫learner。
所謂老了,就是人的心態。有這種心態的公司,就出問題了。我在現在這個位置上,必須要“忽悠”大家去創新。我一直在跟公司領導層尤其是高級領導層講這樣一個概念:你一定會被顛覆掉,不論成功的公司或產品,所有東西都一定會被顛覆掉,或者被別人顛覆,或者被自己。就像所有紀錄都是用來被破掉的,是一樣的道理。
具體到公司層面,我們永遠要想,Windows這么成功了,Office仍然很成功,但是如果我們不創新就會被顛覆。競爭對手有很多了不起的產品,我們真正有希望成功的地方,可能一是對方創新不夠,或者走了一條錯路;二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一定要做得很好。
這種想法,對于站在現在位置的我當然是比較容易,但是具體到產品線的人,他們光是把產品做好就很了不起了,根本沒有精力、時間去想那么多。所以我們之間一定要多做交流,公司有研究院的好處也體現在這里:有一批人不斷地去思考這樣的問題,然后帶領其他人。
在微軟,特別是和研究院有關的事情,我們跟不同的產品部門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產品部門,都有非常暢通的溝通渠道。在微軟,幾乎所有產品設計過程當中,都會主動邀請微軟研究院的同事參與其中,讓他們一起想想能顛覆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要用到語音的話,研究院的人可以告訴產品部門3年以后語音能做到什么地步,這些需要真正懂技術的人幫你解答。
我們也設立了相關機制,以確保領導層知道做出了什么新東西。比如每年有專門向“十一常委”做的匯報,指出那些最有可能顛覆的東西,讓領導了解情況,而后做決策。
我們和比爾(蓋茨)也經常見,他跟我們討論的都是比較技術的問題。他今年60歲,身體很好,腦子很清楚,還老在修理我們,經常就產品的方向、路線和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他覺得很多東西我們做得不夠好,要求比較高。我也覺得自己不夠狠,對手下的兄弟們要求很不嚴格。
很多時候,顛覆的不僅是技術,還有商業模式。微軟的首席經濟師非常出名,他原來去了雅虎做首席經濟師,然后到谷歌,最后被我挖過來。我跟他說,你在谷歌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們根本不需要你,商業模式已經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你還是來微軟吧,因為我們都不清楚。我們在轉型,又換了新CEO,你應該來。現在,他的各種建模做得非常好,對公司有很多貢獻。
這樣的顛覆和創新,于我們而言關乎生死存亡。每個人都知道不創新就完蛋,要么產品不賺錢被關停;要么就是產品賺錢,不創新也不行。資本主義最大的好處就是一定有人跟你競爭。
有人說微軟研究院一直在做不計產出的研究,這是一種誤讀。實際上,從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們就一直強調兩件事情對公司非常重要:其一就是要把計算機科研做到極致;另一個就是要盡快地把科技轉化到微軟的產品當中。
到了最近,除了前述兩點,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公司在轉型,整個高科技界比如軟件、互聯網都在一個新浪潮下。這正是研究院對公司、對行業做出更大貢獻的時機。所以我加了第三點:顛覆技術,創造新的商業——因為前兩點我們已經做得相當不錯,所以在最近兩三年,我更鼓勵大家注重這第三點。
其中到底有什么樣的顛覆性技術是別人沒有想到的,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商業模式,對我們很多做研究的同事來講都是很大的挑戰。但我很有信心,因為微軟研究院也有很多人對產品和市場很有感覺,又和很多的產品部門聯系緊密。所以,微軟最大、最近的轉變,可能就會來自研究院。
王堅說,微軟研究院像幼兒園,沒什么用,但代表未來。這個只有一定道理,因為一開始成立的時候,沒人知道我們能長多大,確實像孩子。但是到今天,20多年過去了,成熟到這個地步,已經有一些豐收的可能了。
 電子發燒友App
電子發燒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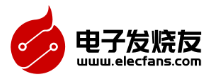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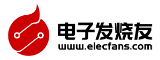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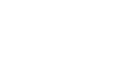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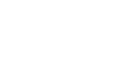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