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鈦媒體App|林志佳 ;在此特別鳴謝!)
馬斯克造出了特斯拉,發射了SpaceX載人飛船,打造了超級隧道,上天入地的埃隆·馬斯克如今又想把芯片植入人類大腦。
給人的腦殼開一個“洞”,把一塊硬幣大小的、帶有傳感器的“芯片”植入進去,到底可以幫人類做什么?
在馬斯克的設想中,一枚芯片可以讓大腦和計算機有了一條通路:“它”可以實時監測你的健康、并警告你是否有心臟病發作、中風等風險;“它”可以模擬催產素、血清素等化學物質的釋放,通過控制激素水平,減輕焦慮,緩解抑郁——對,抑郁癥患者的福音;“它”甚至可以存儲一個人的記憶。
承載腦機接口夢想藍圖的,是他在2017年成立的新公司Neuralink。遺憾的是,今年8月29日,Neuralink公司在第二次成果發布會上出來演示最新技術成果的依然不是人類,而是三只小豬——距離首次發布會過去了一年多,馬斯克的腦機接口研究依然沒完成臨床人體實驗。
人類大腦,這個果凍般的、約占人體體重2.1%的東西,包含近1000億個神經元細胞,藏著人類誕生以來最難破解的秘密,也激發了全球無數科學家和實驗室的探索,但到目前為止,人類對大腦能力和奧秘的開發“還不到大腦真相的1%”。
我們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人類為什么可以不斷發掘腦潛能,卻無法控制大腦?人類生命對終極命題的發問終會歸結到對大腦的無盡好奇。
而更為現實的問題是,癱瘓、腦損傷疾病、阿爾茲海默癥等等疾病對人類的困擾,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質量。腦科學也因此成為全球公認的最前沿也最難的學科。
一位中國企業家領袖的身影,若干年前也開始活躍在世界腦科學界的核心舞臺上,他就是盛大集團創始人,如今的TCCI(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創始人陳天橋。他在今天已經非常不樂于被媒體提起他曾經“31歲就成中國首富”,更不樂于再被提及“至今無人打破這個年齡紀錄”的事實,低調潛身于科研慈善事業。2016年,陳天橋以私人捐贈的方式拿出10億美元,資助全球腦科學的基礎研究,義無反顧。
與馬斯克一樣,陳天橋也希望撬動人類大腦。治療腦疾病也是TCCI資助科研的出發點之一,但他對腦科學領域基礎研究的長期判斷,卻和馬斯克“唱了反調”——他首先反對的就是馬斯克的腦機研究對健康人也要進行“開顱”干預。
開顱,還是不開顱,這是個問題
2020年10月,TCCI首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在大型神經醫學中心上海華山醫院虹橋院區落成,并展示了中美科研專家在腦科學研究不同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最引人注意的一項成果,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Pattie Maes教授在會上展示的如何用嗅覺進行夢境控制。
在會議結束后,陳天橋近期接受了鈦媒體App的獨家專訪。有趣的是,陳天橋把類似這種“嗅覺控制大腦”的基礎研究項目,形容為“特洛伊木馬”、借道攻城方式的一種——而非馬斯克那樣直接“打開腦顱”的“炸開城墻”方式。
陳天橋告訴鈦媒體App,馬斯克通過芯片植入三只小豬大腦獲取信號的方式,并不是革命性的突破。“不論用豬還是拿老鼠來實驗,沒有區別。展示的豬產生了意念和行動,大腦電波自然會動,其實是一個常識。”
但開顱的意義在于“服務臨床治療”,開顱手段在臨床治療上已經愈發成熟。“我一直強調,對于病人,我們應該以治病為主,一切最新技術,一切可行手段都要使用,包括開顱。有兩個案例,那就是我最早投入加州理工就是因為看到了加州理工教授已經完成了對癱瘓病人的電極植入并且指揮機械臂進行操作,甚至可以通過刺激腦部區域讓癱瘓病人直接感受到失去知覺部分的知覺,包括能夠讀取大腦中的想法等,這些都是需要開顱的。”陳天橋對鈦媒體App 詳細闡述了其對于“打開腦顱”的看法,更適用于“治病救人”,而不適用于健康人的大腦研究與開發。
“現在這一路線上的研究重點,是如何讓植入的芯片更安全、信道更多、數據更準確的問題,但這種開顱治療并不屬于革命性的突破。我們支持的中科院微電子所的陶虎教授的新型大腦電極,其實比Neuralink進展更快。”
在前述「腦科學前沿實驗室」成果展示中,就特別展示了陳天橋所提到的項目,由中科院上海微系統所陶虎研究員團隊和華山醫院神經外科團隊共同承擔。
該科研項目最大亮點,是在小鼠的顱內植入“神經元幾乎感受不到的”、超薄、超柔的高通量神經信號采集芯片,通過神經信號處理接口電路直接相連的電腦,來實時反映小鼠活動時的腦電信號變化。小鼠腦中所植入的電極,創造性的使用了絲蛋白這一中國古老材料,據陶虎介紹,“其在植入創傷、長期在體安全性等關鍵技術上已經達到甚至部分超越了Neuralink。”
“但是我們今天討論的共同愿景,是如何能夠讓絕大多數人群,主要是健康人群能夠把大腦直接和電腦互動,這一點上,我和馬斯克的觀點上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能炸開健康人大腦的城墻強行連接和傳輸。” 陳天橋非常明確表達了自己與馬斯克在大腦研究方向上的分歧。
陳天橋認為,真正能帶來技術突破的腦科學基礎研究,不一定要打開腦殼“炸開城墻”,“我們不應該像馬斯克這樣造另一個外腦”。人類完全如“特洛伊木馬”攻城一樣,借用大腦已有的入口,例如耳、鼻、喉、眼、口等五官五感本身就是大腦已經對外有的入口,Pattie Maes教授利用“嗅覺”進行夢境控制的方式,就是通過五感進入大腦。
“如果想要攻破城門,只需要像特洛伊木馬一樣放在城門口。也就是說,大腦有更多類似API插件或者是USB插口,在城門口溝通接入就可以了。首先,利用已有的城門,通過AI編輯遞送的包裹本身的信息,對大腦特定區域的腦區進行干預和互動。現在MIT的教授已經可以通過AI編輯的一段特定信息給猴子看能準確地激活猴子大腦特定區域。其次,利用非侵入式(如ultrasound)或者半侵入式(通過血管倒入納米芯片)把信號和大腦特定區域進行交互。”
“坦率說這兩個方向在技術上比直接動手術更難,我們需要有更長時間的準備,基礎研究不可缺少,這就是我們為什么和學術機構保持持續良好的互動,不斷推進的原因。”
馬斯克在極力的向公眾“秀”出他的快速“成果”,而陳天橋則認為基礎研究不應該急功近利。兩位心懷人類終極命運的創業者,在腦機革命的路上,狹路相逢。
“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路線之爭
2015年,陳天橋雒芊芊夫婦包了一架飛機搬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這個“應許之地”。
這是多年前陳天橋患重度焦慮加驚恐發作(Panic Attack)之后第一次坐飛機。他曾在接受騰訊采訪時說,自己曾先后有三家公司在華爾街上市但沒去敲鐘,因為要飛到紐約;與哈佛和麻省理工合作時,他無法坐飛機,校長們別無他法,只好飛過太平洋來拜訪陳天橋。
搬到加州沒多久,陳天橋做出首個重要決定——建一座腦科學學院,“先期投入10億美元”,他在捐贈儀式上如此承諾。加州理工學院的腦神經科學家Richard A. Andersen教授則被任命為新學院腦機接口中心主任。
連續五年,陳天橋不斷接觸科學家和實驗室負責人,仔細找尋心儀的美國的大學和研究所。
從加州到紐約州,從華盛頓到亞利桑那,過去五年登記在他腦內的頂尖科學家已超300人,28所大學校長向陳天橋描述了未來十年本校在腦科學領域的愿景。鈦媒體創始人趙何娟曾跟隨陳天橋訪問幾家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和若干實驗室,親眼見證了陳天橋如何因為對幾位年輕科學家正在演示的研究項目PPT感興趣,就當場宣布向該科學家捐贈,驚得趙何娟目瞪口呆。
“他果然是動真格的。” 趙何娟在那趟行程后表示。
在學術界,腦科學也被叫做認知科學,一種探索大腦是如何工作的科學技術——如何思考、如何記憶、如何學習等,而腦機接口是其中最為外界熟知的一項。
侵入式腦植入物幫助癱瘓恢復手臂的技術過程
如今,對腦機接口公認度較高的一個定義是:腦機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是在人或動物腦(或者腦細胞的培養物)與外部設備間建立起直接通路,通過腦電波的反饋,讓計算機獲得信息,采集人們大腦中生物的特征值,并把信息翻譯成機器語言,從而反饋到肌體,完成腦和外部設備間的信息交換。
用陳天橋對鈦媒體App的比喻來說,“形象點來說,我們對人的大腦認知控制或者了解,就是要把‘大腦’這座城墻打開一個門洞,來對其進行一定的影響和控制。”
從實現腦機接口應用的技術研究來分類,目前有公認的三類技術路線:侵入式、部分侵入式、非侵入式。
侵入式:在人的頭部打開一個洞,然后利用一個類似立方體的腦機設備,將大約七八厘米左右的電極插入大腦內部,直接采集人們大腦發生的電信號變化,來推測人們的意識。這種目前主要用于重建特殊感覺(例如視覺)以及癱瘓病人的運動功能,或用在SEEG(立體定位腦電圖)當中。
非侵入式:在不破壞人體大腦的情況下,比如通過EEG(腦電圖)、MRI(核磁共振)、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紅外線等方式,去采取人們大腦中非常細微的腦電變化、信號變化,然后對視覺皮層的信號進行模式識別和圖像拼湊,利用大量數據、算法去推測大腦中的信息。
半侵入式:這主要是利用顱內腦電圖(ECoG)技術,將頭蓋骨打開,然后把電極陣列放在大腦的皮層上面,但不破壞大腦,然后把電極插入大腦中,主要進行癲癇的診斷和科研探索等。事實上,這種半侵入式一直都有爭論。因為這種也要做開顱手術,且比侵入式突破的深度層級反到更大,電級要植入到顱腔內才可以。
馬斯克的Neuralink,是典型的侵入式路線的明星公司。
2019年7月16日,Neuralink首次公布了其在腦機接口研究上的“重大突破”:依靠線程(Threads)、機器(Robotics)、芯片(Chips)、算法(Algorithms)四個具體方向,利用手術機器人、N1傳感器和柔性電極三大工具,以侵入式腦機接口方式建立腦-機系統,并成功在小鼠上進行了實驗。
今年8月,馬斯克攜三只小豬再次對外展示了Neuralink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新進展。最核心的變化在于傳感設備的變化,傳感設備縮小到“硬幣”大小(產品名為Link V0.9),并將1024個柔性電級內嵌其中,而神經外科手術機器人V2比前代變得更加智能、快捷,縫合過程大約需要30分鐘,一小時內完成整個腦機植入過程。
然而,針對馬斯克的研究展示,多位業內專家告訴鈦媒體App,Neuralink的這一成果在腦機領域“并沒有絲毫創新”,“鼠狗豬都是必經之路,說明不了什么問題。”
因此,與Neuralink這種侵入式路線來說,非侵入式的方式暫時更被科學界認可:不會介入腦內影響通路,更容易讓普通患者所接受。但是也因為大腦有一個極其堅硬腦殼保護,非侵入式的研究進展很慢,實驗成果暫時并不顯著。
從大腦構造來看,人腦從外到內依次是外層的頭皮、頭骨,頭骨下有三層膜將大腦包裹起來,分別為硬腦膜、蛛網膜和軟腦膜;再往內是大腦皮層(灰質)和白質。
正常來說,侵入式腦機接口設備將會把電極植入大腦皮層,然后反饋信號;而非侵入式腦機設備,類似腦電圖,只是會穿過頭骨但位于大腦皮層外,不會介入腦內影響通路。
從實驗角度看,科研機構以及企業對侵入式技術的實踐十分謹慎。其設備直接從大腦神經元周邊采集信號,或在神經元上直接采集神經元層面的尖峰電位(spike)。盡管它采集的信號精準度很高。但對實驗對象來說,開顱手術目前仍不可避免。而相對來說,非侵入式更易大量實驗。
在非侵入式手段中,用于記錄信號的硬件設備近年來都沒有太大變化,目前不管是相關高校機構,還是商業企業,硬件只是收集數據作用,更多技術提升都在神經解碼環節,利用遷移學習和深度學習等手段,從而獲得更高精度信號。
不過,非侵入式最大的瓶頸在于,如果設備離神經元越遠,相對而言獲得的信號就越模糊。加上數據量不夠,信號準確性很難把握,采集回傳的信息精度大打折扣,信號預處理的難度陡然上升,從而導致腦機接口技術傳輸有偏差。
陳天橋則認為,這一問題可以通過“特洛伊木馬攻城”的方式采集“深層數據”解決。
“實際上,我覺得1000萬人、1億人的實驗,這可能是你們理解的大數據。但是,如果專注把即便只有一個人的大腦數據研究透,這種數據量都已經是足夠多到你無法處理的地步了。后者更多是我們想要做的,我們內部將其叫成深層數據(DeepData),這個才是關鍵數據要點。”
“詳細來說這個深數據問題。其實這個更多的是研究你的行為,比如正常人看手表,看App,社交、睡眠、點頭、眨眼這些動作,我認為這都是數據。那么,捕捉這些數據,然后進行研究,這并不需要你有1000萬人、1億人做這個事情。更多還是在于,你給不給他這個數據,這事更為關鍵。”
陳天橋說,科學家們可以利用這種深層數據,加上機器學習算法等技術手段,在不損傷患者大腦的情況下,可以達到與侵入式一樣的效果和反饋,甚至要超越后者。
TCCI在選擇資助項目和實驗室的最初階段,就一直在尋找那些利用非侵入式(Non Brain)技術方式來解決問題的項目和科學家。“也是因此,(科學家們)研究時間可能要更長,花上5到10年,我希望在這個時間內解決并實現技術應用。”陳天橋對鈦媒體App表示。
他對鈦媒體App說,TCCI資助的研究類型,“侵入式”和“非侵入式”都涉及,但他們主攻利用AI和大數據手段,實現非侵入式腦機交互。不管從倫理上,還是準確和安全性上面,后者在臨床應用層面更能被大眾所接受。
“但我們和侵入式不同點來說,我們就像希臘人藏在特洛伊木馬里那樣,光明正大通過城門進城攻城,而馬斯克的研究方式則是‘炸開城門’,給腦殼開個洞。而我認為,并不需要像馬斯克那樣‘炸開城門’,更多作為API插件或者是USB插口,在城門口溝通接入就可以了。”
對于大腦研究的難點,陳天橋大腦是這樣想的,“縱觀整個人類的工業化歷程,從電力革命到計算機互聯網,都是把人的欲望和「機器」聯系起來,但你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人類很難控制(自己的)大腦?” 按照他的理解,通過不同方式去讀取大腦信息這件事,人類已經做到了,最難的是,“研究人類對自己大腦的控制機制”。
Neuralink向左,TCCI向右
被稱為“腦機接口之父”的美國杜克大學醫學院神經教授米格爾·尼可萊利斯(Miguel Nicolelis),在今年11月的騰訊科學大會上接受鈦媒體App采訪時說,“馬斯克講的這些,我一個字都不同意。”
尼可萊利斯教授的的觀點,更接近陳天橋的邏輯。他認為,Neuralink公司的思路是一個死胡同,侵入式腦機接口技術僅適用于那些特別嚴重的神經系統受損患者,即完全癱瘓的病人;而對于大部分患者來說,更建議采取安全性較高的非侵入式腦機交互技術。
“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擔心,因為我本人不只是一個神經學家,我還是一名醫生。作為醫生,我認為患者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人和動物畢竟不一樣,對動物做研究,在它的大腦和身體里放入植入物,這個研究我們已經做了38年,包括猴子、老鼠,我們能夠確保這些實驗動物的安全。”尼可萊利斯告訴鈦媒體App。
因此,因為有了在“侵入式”還是“非侵入式”技術路徑的不同判斷的基礎上,與馬斯克的Neuralink不同,陳天橋創立的TCCI研究院也選擇了不一樣的運作模式。
TCCI資助科學家團隊的前提,是陳天橋為TCCI的發展設計了完整的規劃。在前沿腦科學領域,TCCI的研究基石是以人腦精準度(Precision)、醫學性(medicine)為概念,通過對人行為的數據收集,對大腦區域的研究,準確獲知人的大腦信息,從而找到信息和區域的對應關系;然后利用AI、大數據等手段,將信息篩選、歸類,形成一種特定激活區域的腦機處理能力;最終在非植入大腦物體下,實現腦機交互,并期望將對用戶進行治療或者認知改變。
差異一:出發點不同
對于馬斯克提出的宏達設想,陳天橋認為,目前有兩個問題沒辦法解決:一個是技術實現路徑問題;另一個是倫理問題。
“開腦洞”對人腦的傷害是顯然易見的。正是由于馬斯克對輿論的影響足夠大,媒體和公眾普遍忽略了對于‘病人’的關注,還有技術手段對人的傷害。TCCI對技術路徑的判斷,出發點也是站在臨床角度,或者說患者角度考慮,“以最不受傷害的方式,可以取得同樣的作用,并不一定需要像馬斯克這樣去損害完整的生命體。”
從倫理角度而言,陳天橋表示,“人的倫理在于心。再怎么安全,心是永遠很難打開的。先不說患者,僅僅就說我們健康人,在腦袋開個洞、再植入異物,沒人愿意這樣做。”
TCCI在基礎研究項目的篩選標準,直接體現了他與馬斯克的本質不同。TCCI主要聚焦大腦探知、大腦相關疾病治療和大腦功能開發三大領域的研究,包括腦機接口、睡眠夢境、認知評估、數字醫療等多項科研內容。
通過這個定位,陳天橋找到了MIT(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教授Pattie Maes、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神經工程中心主任Edward Chang等人,資助他們開展腦機研究。
在美國“地毯式”搜尋科學家和項目兩年之后,TCCI的資助正式落地中國。考慮到中國在腦科學基礎研究層面還有一定距離,TCCI在中國的捐贈,主要包括與華山醫院和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合作,以及通過這一窗口建立實驗室。
3年后,TCCI的中國之旅再進一步。10月23日,TCCI與華山醫院的合作取得了最新進展,首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在上海華山醫院虹橋院區落成。
在落成儀式上,Edward Chang教授回報資助之恩,首次發布并展示了其所在實驗室的“讀心術”最新成果:采取植入式腦機接口技術解碼語言信號,解碼速度接近正常說話,準確率達到97%,并且對患者的腦部傷害達到最低。
同樣在這場會上,來自中國的科研團隊也展示了在夢境檢測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睡眠和夢境實驗室里,一位年輕男子躺在監測床上,全身密布電極、線路,這是傳統用于睡眠障礙監測診療的PSG設備。而一邊的年輕女孩,僅僅需要頭上貼著一片薄薄的電極貼,就可以實時監測睡眠腦電、呼吸、心跳等多個重要指標。在技術路線的分類上,這是典型的“非侵入式”臨床手段。
“技術對人類大腦的傷害程度如何”,是陳天橋在選擇資助項目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他向鈦媒體App表示,不管外界如何看待資助這件事,TCCI這家科研機構依然需要支持全球科學家開展腦科學方面研究,這既是他對社會的責任,也是為人類腦科學發展造福的一條重要路徑。
“我們TCCI搜遍世界上的科學家和實驗室,通過5~10個實驗室,建立早期的技術模型,不但要資助,而且要將最具潛力、前途的科學家挖進我們的實驗室,給他們學術自由、給他們資金,讓這些科學家發揮才能,能夠做出一個非侵入式的,為人類造福的腦科學技術解決方案。”
差異二:規劃不同
在創立Neuralink之初,馬斯克多次談及未來規劃目標,諸如25年內Neuralink將有望開發出全腦接口(Whole Brain Interface),即讓人類所有的神經元和AI載體連接在一起,這聽起來的確頗為科幻。
相對于馬斯克的科幻論調,陳天橋提出的是穩扎穩打的“三步走”研究規劃:大腦研究(Brain research)、臨床治療(Brain treatment)和腦網絡,這也是他在創立TCCI之初就已經清晰的規劃。
第一階段是基礎研究即大腦研究(Brain research),在細胞和分子層面搞清楚人類大腦運作的機理;
第二階段是臨床治療(Brain treatment),主要通過神經科學手段治療困擾人類的三大類腦疾病(精神性疾病,退行性疾病和其他大腦生理性疾病);
第三階段是大腦發展。這一階段將運用AR或VR等技術推動神經康復,為新一代人工智能奠定基礎。
“未來我們想要做Brain development,也就是腦發展網絡,就是說如何能夠在大腦研究的基礎上面,讓大腦變得更強壯,包括利用AI技術、AR/VR等,還有你大腦的vision視覺,重新創造和感知這個世界。”陳天橋對鈦媒體App表示。目前,按照TCCI的規劃和進展,第一階段已經“做到一半”,第二階段則正在進行中。
Neuralink天然要更關注商業模式和技術的普適性,腦機接口技術應用的市場;而陳天橋則是通過資助基礎研究,定義從基礎科研到商業落地的邏輯。
除了上述的技術“三步走”之外,陳天橋對鈦媒體App強調,TCCI不介入科研研究,只是資助身份,讓科學家放開手腳去做一些很重磅的研究課題,只要最終能夠落地,對人類有貢獻,有幫助,足矣。將“不計成本”的支持科學家開放研究。
TCCI成立以來,他個人的精力主要放在美國基礎科研領域,尋找專業的科學家;而在中國腦科學前沿實驗室的建設上,由TCCI轉化中心主任、華山醫院院長毛穎教授領導。陳天橋認為,私人方式資助基礎科學研究,是回報社會最好的方式。
極具輿論影響力的馬斯克,曾表達過他研究腦機接口的初心,是“為了避免人類被人工智能控制”,終極目標是讓“全腦接口”能力在全人類實現商用;而陳天橋的目光則放在了下一個十年的產業革命上,他曾提出,下一次產業革命的基礎是認知科學。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之間,馬斯克與陳天橋兩位腦機接口的靈魂人物也在相互關注對方,雙方約定能在疫情穩定后面對面進行一次深度交流。盡管兩人的技術路線不同,獲取回報的路徑更不同,但他認為,馬斯克和他有著同一個最終夙愿——造福人類健康。
(本文首發鈦媒體App,作者|林志佳,編輯|蔥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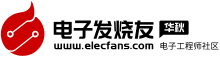
 人腦植入芯片的危害有多大?大腦芯片植入技術路線的探討
人腦植入芯片的危害有多大?大腦芯片植入技術路線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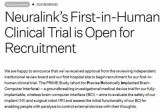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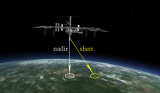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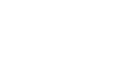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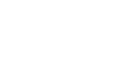





評論